狄拉克与徐志摩一样喜欢在剑桥散步,但他追求的是物理规律的数学美。那么,到底是徐志摩的诗美,还是数学美?狄拉克说:“科学是以简单的方式去理解困难事物,而诗则是将简单事物用无法理解的方式去表达,两者是不相容的。”
沉默寡言的狄拉克
英国物理学家保罗·狄拉克1902年出生于英格兰的布里斯托,他对量子理论的贡献可说是无与伦比。他在1925-27年所做的一系列工作为量子力学、量子场论、量子电动力学,及之后的粒子物理奠定了基础。
狄拉克的科学风格是精确,性格特点则以沉默寡言著称。你听过“狄拉克单位”吗?它不是狄拉克在物理学中的创造,而是当年剑桥大学的同事们描述狄拉克时所开的善意的玩笑,因为他们将“1小时说一个字”定义为1个“狄拉克单位”,由此可见狄拉克言语之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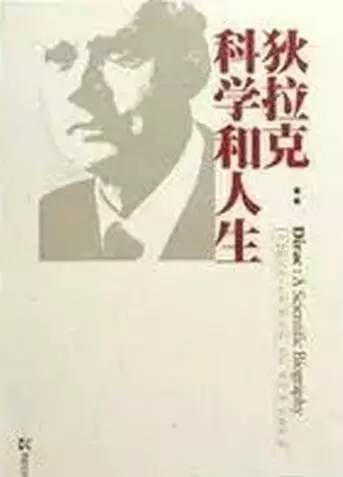
狄拉克的少言寡语不知道是不是现代人常说的‘自闭症’。但据说很可能与他少时成长的家庭环境有关。狄拉克的母亲是英国人,而父亲是来自瑞士的移民。父亲是一位法语教师,对家人严厉而专制。他规定孩子们在家只能说法语。据狄拉克自已的回忆,家中完全没有社交气氛,即使是家人之间,话也极少,每次用餐之时,母亲和狄拉克的哥哥费利克斯,以及妹妹坐在厨房里吃饭,而狄拉克和父亲两人则坐在餐桌上。狄拉克的法语不好,英语父亲不要听,因此,他便宁愿选择不吱声,什么也不说。后来,狄拉克和哥哥费利克斯同在布里斯托大学,同学工程,兄弟俩街头碰见擦肩而过也互不言语。因此,狄拉克从小就对家人间无交流的现象习以为常,以为家家都如此。后来,事故终于在沉默中爆发,1925年,狄拉克的哥哥费利克斯自杀身亡。所以看起来,哥哥的自闭症状恐怕还胜于狄拉克的。对兄长之死,狄拉克亲见父母悲痛万分,他才恍然大悟,明白家庭成员之间还有亲情。狄拉克后来回忆时说:“我那时才知道,原来父母亲是很在乎我们的。”
狄拉克是一个少见的“纯粹”的、真正学者型人物,波尔曾说:“在所有物理学家中,狄拉克拥有最纯洁的灵魂。”他除了不说废话之外,物质生活上也极为简单,不喝酒、不抽烟、只喝水,别无他求。其它方面的兴趣也很少。最大的业余兴趣就是‘散步’。
剑桥大学位于风景秀丽的剑桥镇,著名的康河横贯其间。狄拉克每天的早晨和傍晚,都悠然漫步在校园内、康河旁,每个星期天便带着午餐步行一整天。说到剑桥和康河,我们中国人最容易联想到的是著名诗人徐志摩的绝美诗篇《再别康桥》:
“轻轻的我走了,正如我轻轻的来;我轻轻的招手,作别西天的云彩。那河畔的金柳,是夕阳中的新娘;波光里的艳影,在我的心头荡漾……”

同样是上世纪的二十年代,同在剑桥,都爱散步,两人都是一边散步一边思念梦中情人。也许中国的诗人和英国的学者曾经擦肩而过?不过可以想象,即便碰头,他们心头荡漾的波光艳影却完全是两码事。徐志摩思念的是林徽因,狄拉克念念不忘的梦中情人却是量子力学,那一代年轻物理学家集体追求的‘小妖精’。
狄拉克特别追求物理规律的数学美,到底是徐志摩的诗美,还是数学美?有关科学和诗的比较,狄拉克有一段精彩评论,令人听后定会芜尔一笑。他说:
“科学是以简单的方式去理解困难事物,而诗则是将简单事物用无法理解的方式去表达,两者是不相容的。”
1925年夏天,是剑桥最美的季节,康河一泓碧水,两岸垂柳成荫,海森堡来到剑桥访问。
当时,量子论的三个研究中心分别是德国的慕尼黑大学、哥廷根大学、和丹麦的哥本哈根大学,狄拉克在英国有点算是孤军奋战。海森堡与狄拉克年龄相仿,个性却完全不一样。海森堡能言善辩,大胆质疑,他就是在1922年在玻尔的一次演讲会上对波尔直言不讳、激烈辩论而被波尔看中招到哥本哈根去作研究的,当时他才21岁,正是“初生牛犊不怕虎”的年龄。有关海森堡与狄拉克个性迥异这点,后来还有一个有趣的小故事:1929年海森堡与狄拉克一同去日本参加学术会议。海森堡喜欢社交,在晚会上经常与女孩子跳舞,狄拉克则只是静坐旁观。一次他问海森堡为何这么喜欢跳舞,海森堡说:“和好女孩跳舞是件很愉快的事啊!”狄拉克听后沉思无语,过了好几分钟之后冒出一句:“还未测试之前,你如何能判定她是或不是好女孩呢?”

还是回到1925年,海森堡到剑桥访问之前。当年的海森堡染上了一种流行热病,脸肿得像烤出来的大圆面包,以至于把偶然撞见他的房东吓了一大跳,还以为是他和人打架而致。因此,海森堡不得不去到北海的赫尔格兰岛,休养一段时间。那个暂离喧哗的小岛,倒是激发了海森堡非凡的科学灵感,他构想出了他对量子力学的最新突破-后来被称作“矩阵力学”的理论。海森堡虽然为这新思想而激动,但又心中无底,不知到底是对是错。因为他的理论中得出的矩阵乘法互相不对易。我们现在对不对易的矩阵已经司空见惯,而海森堡等物理学家在那之前,却还不知道矩阵为何物,因此,他为这‘不对易’性而惶惶不安。所以,在剑桥访问期间,海森堡对自己的矩阵理论表现得很低调,只在一个小型俱乐部的学术报告中提到了自己这方面的工作。当时,狄拉克不是那个俱乐部成员,所以没有去听这次演讲。而直到两个月之后,才从指导教师福勒那儿得到了海森堡的文章。福勒希望听听狄拉克对海森堡艰涩难懂的量子力学矩阵描述有何看法。
那是1925年九月的一个周日,狄拉克一如既往地带着午餐散步一整天。他望着剑桥大学各个学院瑰丽庄严的古堡式的校舍建筑,周围康河边美不胜收的绮丽风光,脑海中总在盘旋着海森堡那个奇怪的乘法规则:p×q≠q×p。尽管海森堡本人对此感到困惑,狄拉克却直觉地认为这正是新理论的精辟之处。并且,精通数学的狄拉克看着那个不等式觉得眼熟,似曾相识。在哪儿见过呢?突然,脑海中灵光一现,狄拉克想起了经典的泊松括号,与此不是很相似吗?
后来,狄拉克由泊松括号和海森堡的矩阵表格再继续想下去,悟出了隐藏在海森堡矩阵力学中深奥的代数本质,创造了互不对易的所谓‘q数’,以及这些‘q数’之间的运算规则,并以此发展出一个漂亮的量子力学符号运算体系。之后,狄拉克又再一次的‘灵机一动’,形式地将泊松括号拆开为左右两半:分别叫做左矢<|、右矢|>。这成为表示量子态的著名的“狄拉克符号”。如此美妙而又深奥的形式数学,都是狄拉克悠哉悠哉地沿着康河散步的产物,是狄拉克谱写的“再别康桥”式的美丽数学诗篇。
紧接着,薛定谔将德布罗意波的概念扩大到了一般量子体系的波函数y(x),又得出了波函数所遵循的波动方程,狄拉克及时跟进,证明了薛定谔方程和海森堡的矩阵力学两者既互相等价,又彼此互补。这个结论使得喜欢微分方程,讨厌矩阵的物理学家们大大地松了一口气。
狄拉克十分追求物理理论的‘数学美’,其实这点与徐志摩一类的诗人追求的‘意境美’是一致的。狄拉克喜欢单独一人玩数学,摆弄方程式,量子力学在他神奇的手里玩来玩去,最终被极为美妙地数学化、形式化。他将众物理学家们养大的这个‘量子妖精’,用逻辑清晰,简洁而奇妙的数学理论,装扮成了一个清纯美丽的天使。
据狄拉克自己声称,大学时代接受的工程教育对他的物理研究工作影响深远,使他明白了做科学研究时要“容许近似”。不可能有‘完全正确’的方程式,而近似的理论照样能表现出惊人的‘数学美’。他创立的狄拉克-d函数即为一例,这个不符合经典函数理论的怪异函数,最终在物理和工程中被广为应用,不仅成为科学家和工程师们处理不连续情形时最强有力的工具,而且成为最早定义的‘广义函数’,由此启迪了泛函分析这个函数论发展中的重要分支。狄拉克对数学美极端追求,以至于在1963年《美国科学人》的一篇文章中,他写出如此超凡脱俗的话:
“使一个方程具有美感,比使它去符合实验更重要。”
狄拉克的另一个重要贡献是著名的狄拉克方程,我们将它的导出过程留到下一次介绍。
有了狄拉克方程后,狄拉克为了追求他的理论的数学美,而作出了一个被称为‘狄拉克海’的、能自圆其说的美丽假设。在这个假设的‘狄拉克海’中,有可能会出现一些‘空穴’一样的泡泡,类似于电子,但却带正电荷。换言之,狄拉克基于对数学美的追求,预言了当时并不存在,似乎显得有些荒谬的正电子。

可没想到,在1932年,从美国加州理工学院传来一条令人吃惊的消息:卡尔·戴维·安德森(Carl David Anderson)在研究宇宙射线的云室里,发现了一种与狄拉克假设的‘空穴’一模一样的新粒子-正电子!这是人类第一次发现的反物质,这个实验为狄拉克赢得了1933年的诺贝尔物理奖。卡尔·戴维·安德森之后也因此发现而得到了1936年的诺贝尔物理奖。
狄拉克当时对卢瑟福说,他不想出名,想拒绝这个奖。卢瑟福对他说:你如果拒绝了更会出名,别人会不停地来麻烦你。听了卢瑟福的话,狄拉克才欣然前往,在领奖典礼上作了一个‘电子和正电子理论’的报告。
也许正因为过分重视理论的数学美,狄拉克后来非常反对理论物理中的重整化理论,认为这种为克服无穷大而采取的权宜之计破坏了量子电动力学的美丽。由于拒绝接受重整化,狄拉克后来逐渐远离了理论物理研究的主流。1970年,将近70岁的狄拉克携家带口来到美国定居,受聘于弗罗里达州立大学。
14年后,狄拉克长眠于弗罗里达,留下他毕生追求的数学美永照人间。
来源:张天蓉博客
编辑:wqd
